元宵拾趣
文/李娜(辽宁朝阳)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儿时的民谣,一直抓挠得心里痒痒的,却一直没能目睹这般奇景。不过令人惊喜的是,我竟有幸亲眼见证了元宵蹦到小碗里的情形。
正月十五月圆夜,我在出租屋内第一次亲手炸元宵。夜晚的阳台,可以看见璀璨的星光,却也是彻骨的寒冷,我只得在卧室里进行:刷锅,开火,烧干锅壁上的水珠,倒入适量的葵花籽油,待油温上来后,开始放元宵。“刷”的一声,滚圆的元宵,便开启了神奇的油锅之旅。眨眼的瞬间,只见油花在锅底翻江,元宵在油中蹈海。我蹲在锅旁,握着筷子的最上端,像儿时点鞭炮一样,戳一下就躲得老远。一会儿功夫,元宵一个个充了气似的,鼓鼓的,在油面打旋。紧接着,只听锅里砰砰作响,它们约好了似的,在那一刻释放出洪荒之力,一个接一个地爆开。有几个脾气甚是火爆,竟然从锅里迸溅而出。有的在地板上打滚儿,撞到桌角才停下来,有的竟直接蹦进了床头的小碗里,然后突然就变得安静。
那一刻,突然就想念在老家过元宵节的情景了。那时候吃的元宵,都是蒸的,像腊月蒸豆包、蒸年糕一样,在篦帘上铺一层“菜帽子”,就是为了便于存放晾干的白菜叶子,既能防止元宵受热后顺着篦帘的空隙漏下去,又有一种淡淡的菜香。奶奶将元宵整齐地在上面摆成圆形,象征着团团圆圆。我就坐在爷爷用苞米皮编成的蒲团上,点火,加柴。
多年后方知,在北方,元宵是“滚”出来的:以馅为基础,和匀后摊成大圆薄片,晾晒后切成小块,然后放入像大筛子似的机器里,倒上江米粉,“筛”起来。随着馅料的互相撞击,江米沾到馅料表面变成球状,就成了元宵。而这江米粉粘性大、透气性差,加之油温过高,元宵内外受热不均匀,外皮炸硬了里面的馅料才开始受热膨胀,所以会爆裂,甚至整个元宵都会飞溅而出。为防止溅出的热油和元宵烫伤自己,可在下锅前用牙签在元宵上扎两个小孔。另外,用小火温油炸出的元宵香甜可口,外酥里糯。
记忆中,元宵节这天,我们还会做花灯。先在装白酒的纸盒上画出自己喜欢的图案,用铅笔刀把图案抠空,然后将蜡烛点燃,在盒底滴几滴蜡油,把蜡烛熄灭坐在上面,最后在镂空处糊上一层薄纸。如此,一个简易的花灯就成型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爷爷边用筷子打着鼓点儿,边哼着秧歌曲儿;奶奶托着花灯,在屋里迈着十字步;我则会用一根木棍耍把式,摇身一变成了神通广大的孙猴子。耍累了,就挑着花灯学起了更夫,嘴里还念叨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眼看着,元宵佳节将至,记忆中的一幕幕又如过电影般浮现在眼前……
小链接李娜,笔名风凝,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蒙古族,中共党员,辽宁省作协会员。曾获第八届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大赛一等奖;“春风十里桃花红”征文二等奖;“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征文一等奖;“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征文二等奖等。作品散见于《西部散文》《人民周刊》《人民代表报》等50余家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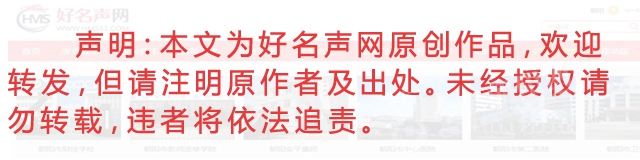
[编辑 熙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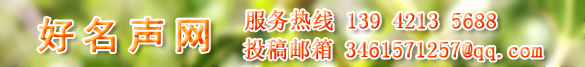


 【好名声网】母亲的“谎言”(包明丽)
【好名声网】母亲的“谎言”(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间烟火年味浓(杨广大)
【好名声网】人间烟火年味浓(杨广大) 【好名声网】我的菜 我的爱(包明丽)
【好名声网】我的菜 我的爱(包明丽) 【好名声网】鸡蛋,鸡蛋(李娜)
【好名声网】鸡蛋,鸡蛋(李娜) 【好名声网】展开梦想的翅膀(杨广大)
【好名声网】展开梦想的翅膀(杨广大) 【好名声网】火锅飘香(王铁兰)
【好名声网】火锅飘香(王铁兰) 【好名声网】流逝的缝补(管丽香)
【好名声网】流逝的缝补(管丽香) 【好名声网】场院(李兴坤)
【好名声网】场院(李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