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道和磨道
文/李兴坤(辽宁北票)
闲来听歌,那“毛驴儿拉磨啊,它走不出那个圈。井里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呦……”带着缕缕乡愁的歌词如一道刺眼的光线,穿透记忆的网,把我带回那个贫穷落后的山沟沟。
记忆中,儿时与母亲走过最多的地方就是碾道和磨道。那时候,村里没有现代化的加工厂,碾子和石磨就是人们磨米磨面的唯一工具。庄户人家都养着牲畜——驴、马、骡子,因而拉碾子拽磨盘的活自然就交给了它们。
我们的村子不大,只有30户人家,但是却有两个碾道,两个磨道,这绝不是奢侈,因为这两个碾道和两个磨道承载着全村人粮食加工的重任。我曾一度感到好奇,那么沉重的石碾,居然是个巧家伙。红高粱去壳,几乎伤不到米;玉米粒破成碴子,就是半碎,玉米吃面,能压到细碎。
记忆中碾道几乎天天有人影,我的母亲白天忙碌,便常借着月光去碾道,那吆喝牲口的声音,筛面拍打箩圈的声音,就是美妙的乡村小夜曲。
碾道最繁忙的时节是腊月,因为进了腊月,乡亲们开始蒸豆包,豆包外皮用大黄米做。自家种的黍子要先去皮,用箩和簸箕一遍一遍筛簸,黍子变成金黄色的大黄米,将其淘洗、晾干,再上碾子经过数次碾压,压成面。淘米后,就要准备杀猪灌肠用的高粱面或是荞面了。无论是黄米面,还是灌肠子面,母亲的要求都很高,光看墙上那些规格不一的箩,你就能猜想出来。我佩服母亲,她可以用一把小笤帚把碾盘上那些被挤压得东奔西跑的米粒圈在一起,一粒不落,眼看着它们由粒变成面,经母亲手中的箩一遍遍筛,最后分类装进袋子里。我也曾学着母亲的样子去扫面,可不是笤帚被碾盘压住就是和驴撞上,尽管这样,我仍愿意跟母亲去碾道,一来给母亲做个伴,二来也可以给母亲打打下手。
磨道的忙碌是分季节的:五月节,八月节,过年。每到这三个节日,家家户户都要泡上几升豆子做豆腐吃,乡亲们认为豆腐是最好的菜,简单省事还有营养。磨豆子与碾面不同,不能贪黑,所以乡亲们都早起。按照先后顺序用水桶或是驴套排队,排到谁家了就打发我们这些小孩子去叫一声。父亲将泡好的豆子用水桶挑到磨道,母亲将自己家的驴套好,与碾面一样,用布将那驴子的眼睛蒙好,还要给驴子戴上箍嘴,防止它偷吃。磨盘转动起来,母亲一瓢一瓢地将水桶里的豆子连同水填进磨盘中间的那个窟窿里。豆子在两个磨盘的研磨中变成白色的液体顺着磨盘的边缘流下,最终汇集到磨盘底下的大盆里,父亲再将它们挑回家,倒进锅里,进行下一道工序。
来来往往的人,谈笑着,小路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和那些洒落的水痕,磨道里回响着男女老少欢快的笑声。
渐渐地,加工厂轰隆隆的机器以精细、快速取代了石碾石磨,做豆腐也不再是逢年过节的大事了,而我仍然怀念我们小村的碾道和磨道,怀念粮食那种原始的醇香,怀念与母亲共同走过的岁月……
小链接李兴坤,中共党员,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辽宁省北票市大三家镇小巴里小学教师。2010年被评为北票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2014年被评为朝阳市级骨干教师,2017年被评为北票市优秀教师,2019年被评为朝阳市优秀教师。2020年参加“朝阳市骨干教师技能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爱好文学,常用朴素的文字记录美好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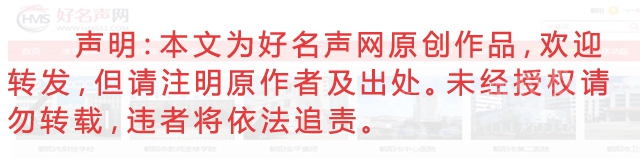
[编辑 直观 编审 春语]





 【好名声网】赶 考(时春华)
【好名声网】赶 考(时春华) 【好名声网】我的父亲(王文月)
【好名声网】我的父亲(王文月) 【好名声网】掐谷子(王铁兰)
【好名声网】掐谷子(王铁兰)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荤油拌饭(石玉梅)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荤油拌饭(石玉梅) 【好名声网】我的爷爷(王洪洋)
【好名声网】我的爷爷(王洪洋) 【好名声网】多情的香雪兰(王劲松)
【好名声网】多情的香雪兰(王劲松) 【好名声网】母亲的线笸箩(李兴坤)
【好名声网】母亲的线笸箩(李兴坤) 【好名声网】老叔的“小棉袄”(王洪洋)
【好名声网】老叔的“小棉袄”(王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