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里那些叫人无法忘怀的游戏——抬花轿
文/时春华 图/胡忠玲(辽宁北票)
小时候的游戏,真是五花八门,有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虽然闭塞,但孩子们还是很有玩的灵性和创造性的,常见的游戏玩腻了,我们竟然会自创花样,这花样让人啼笑皆非,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笑。
农村的小地界,名贵的花草没有,但是打碗碗花、爬山虎花可是开得热热闹闹。爱美的女孩摘上一把绑在发辫上,或掖在鬓角旁,便有淘气的男孩子起哄:“唉,唉,新媳妇,新媳妇。”男孩女孩便追打开来。那时候,就觉得只有新媳妇才会在发辫上插一朵花,因为电影里就是这么演的。那时候,我们的认知很单纯,电影里穿破衣服戴草帽的就是穷苦人;穿锦缎的就是地主;穿绫罗绸缎、戴瓜皮帽、梳长辫子的就是地主的狗崽子;穿黑衣白褂,狗仗人势露着大金牙的就是坏蛋是狗腿子;和坏蛋抗争,眉清目秀的就是好人……那时候演得热闹的电影是《王老虎抢亲》《姐妹易嫁》什么的,我们小孩子就是看个热闹,但是也能看懂剧情,知道娶媳妇是要抬花轿的,于是我们就提议玩抬花轿。
抬花轿,就要有“轿夫”,“轿夫”可得是男孩子,至于“新娘子”嘛,那必是女孩无疑了。小孩子的游戏,说白了就是过家家,但是也得有模有样,像唱戏一样,提鞭为马,伞开雨来。于是我们便五个人一伙,三男两女,两个女孩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是“新娘子”,三个男孩用手心手背决定哪两个人当“轿夫”。选择完毕,出局的两个人就四外寻找打碗碗花、牵牛花打扮“新娘子”。有的孩子爱动脑,就用茅草编一个长辫子,给“新娘子”长长地拖在身后。一切准备停当,“新娘子”就要坐上花轿了。当“轿夫”的两个人,分别用自己的右手握住自己的左手腕,形成一个直角,然后对面互搭,就形成了一个结实的“轿子”。“轿夫”小心地蹲下去,“新娘子”小心翼翼两脚岔开,自“轿夫”胸前的空档穿过,稳稳当当坐在“轿夫”用手臂搭成的“轿子”上。两人慢慢起身,开始左右摇晃“新娘子”,一边摇晃还一边歌谣似的唱说:“小小子儿,胖墩墩儿,长大要不要媳妇儿。”然后自己再回答:“要。”使劲晃,晃得当“新娘子”的迷糊了,倒在谁那一边才算完,倒在谁那一边就成为了谁的媳妇。嬉笑一番,游戏重新开始。那时候就是小孩子,谁成为谁的媳妇都无所谓,但孩子们玩得起劲,也有自己的审美,“媳妇”都爱选漂亮的,“新郎官”都愿意要帅气的,要是很称心的那种,别人起哄也美滋滋的,不般配的那种,也会佯装生气撅嘴的,围着房子转着追打那些起哄的人。有时候人不够,清一色的男孩子或清一色的女孩子也玩这个游戏,玩得热火朝天。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春天里那个百花鲜。我和那妹妹啊把手牵。又到了山顶我走一遍啊,看到了满山的红牡鹃……”火风一曲火爆的大花轿,让我想象着那个坐在轿子里的幸福的女子,想起了我幼稚的童年游戏。我想假如那时候有这么美的歌唱着,有很漂亮的服装穿着,游戏该多有意思。不过,我如此的想法只限于那时。在今天,我如此的想法如果搬上舞台,那就不叫游戏,经过了艺术加工,就应该叫做舞蹈了。
小链接
胡忠玲,辽宁省北票市大三家镇小巴里小学高级教师,爱事业,爱生活,勤奋务实,纯朴善良。时春华,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现就职于辽宁省北票市教育局信息中心。1992年毕业于朝阳市第一师范学校,选修音乐,酷爱文学,文风朴实接地气。热爱生活,热衷传播社会正能量。系朝阳市作家协会、辽海散文学会、北票市作家协会会员;《好名声网》特约助理编辑,此网站有《时春华好名声展馆》;《北票市报》特聘记者,此报刊有专版《朝花夕拾》。在网络、刊物上发表作品60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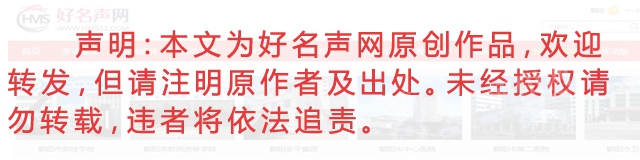
[编辑 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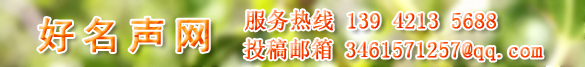


 【好名声网】六一啊六一(时春华 杨晓芳)
【好名声网】六一啊六一(时春华 杨晓芳) 【好名声网】桃三杏四梨五年(时春华)
【好名声网】桃三杏四梨五年(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心中的尺子(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心中的尺子(时春华)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春灌(时春华)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春灌(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的肩膀(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的肩膀(时春华)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温馨家园开展“迎立春,闹元宵”文化体验活动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温馨家园开展“迎立春,闹元宵”文化体验活动 【好名声网】博览群书 一生充实(王铁兰)
【好名声网】博览群书 一生充实(王铁兰) 【好名声网】挂钱儿是大年的彩旗(时春华)
【好名声网】挂钱儿是大年的彩旗(时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