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糗事一箩筐——做毛毽
文/时春华 图/聂雪(辽宁北票)
见啥眼馋真的是所有小孩子的天性,只是女孩子表现得比较外在,男孩子表现得比较内敛而已。小时候,看见别人家的小女孩穿了新式的花衣服,扎了好看的发辫,或是发辫上扎了别致的头绳、发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发夹,自己的小心眼里都羡慕。男孩子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要是同伴谁的手里有别样的pia ji 或者是彩色的玻璃球,那也是屎壳螂跟着屁哄哄,围着人家问东问西抢着看。
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邻居菊花有个姑姑从唐山回来,给她带回个毛毽。小孩子嘛,都属于狗肚子装不了三两苏子油,有啥都要显摆显摆。她把这毛毽一拿出来,可是吸引了所有孩子的眼球,不光是女孩,男孩子也蹿上来了。四五个薄薄的铁片,中间有个绿豆大小的眼儿,眼儿里是一大撮像盛开的花一样的粉色绒鸡毛。看着好看,踢起来也很轻巧。可是,她家的大人老往回经管她,怕我们这帮“土匪”把她的毽子玩坏了。我们的小心眼里,有些许的不愉快。切,就那破玩意,我都会做。
这还真不是吹牛,因为在看毽子的时候,我已经认真观察了,不就是铁片中间戳个眼儿放上一撮鸡毛吗?搥紧了找点塑料一烧,再在平板上摁平不就得了吗?回家之后,我就开始翻箱倒柜找罐头盒盖,拿五分钱的硬币做制子,用剪子剪成五分钱硬币那么大小圆溜溜的圈,中间用剪子尖儿挖个洞,四个圆圈准备做个毛毽。在找剪子的时候,我还发现了爸爸扔在匣子里的几枚大钱,呵呵呵,多现成的东西,怕挨打,我没敢多动,就拿了一枚,找好了蜡烛,塑料,还有一块铁砧板。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缺啥啊,缺鸡毛,确切说是公鸡毛。
其实鸡毛是不缺的,农村,几乎家家养鸡,有时候溜溜达达在街上走的大公鸡比街上玩耍的孩子都多。我们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开始琢磨这原材料。人绝对是有私心的,自己家的鸡都舍不得,于是我们就偷偷在大街上走着踅摸,看谁家人没出来,孩子还小,公鸡还好看、毛多。实际上公鸡到了冬天毛都很厚,因为那是它取暖的必须。好半天也没发现在街上溜达的公鸡。转过弯,忽然看见在狗剩子家墙根儿,有五六只公鸡,我感觉,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里当时一定是贼光闪亮了。大家一哄而上,各撵各的,结果,撵了个暴土扬长,鸡飞狗跳,也没抓住一只。这公鸡真是狡猾,它们不走直线,眼看要追上了,抓住了,人家来个急转弯,侧身跑了,我们急刹车差点摔倒,蹚起一溜烟尘。怕附近的人家起疑心,我们赶紧悄悄地换地方。
不是说该死的鸟往枪口上撞,该死的兔子往油锅里蹦……呵呵呵,就是那么凑巧,没走几家,前面一只漂亮的大公鸡就在那“咔咔”踱步,傲视着我们。我们几个一挤咕眼睛,合围上去。呵呵,美丽的大公鸡就被我们抓住了。爱嘚瑟的五月用手拨拉了一下公鸡的嘴,连说带唱背起了他学过的课文:“公鸡公鸡真美丽,大红冠子花外衣。油亮脖子金黄脚,要比漂亮你第一。”我们没人夸五月,因为有大事、正事呢——薅鸡毛。公鸡的毛属脖子上的软和漂亮,不够的话,腿上的也凑合。老黑逮着公鸡,几个人你一把,我一把就下手了。老黑一手掐着鸡头一手掐着尾巴,直到大家说行了,他才把公鸡撒开。这鸡一放开,大家都快笑喷了。指着喜子说:“喜子,你看这公鸡,跟你爹差不多。”“你爹才这样呢。”喜子有点急眼。实际上,那只公鸡被薅得真有点像喜子爹,喜子爹秃头顶,四外有点头发也不多,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秃咕噜腚子”,要不人家喜子咋不乐意啊。
回家之后,兴奋异常地戳鸡毛,把鸡毛钻过大钱眼儿和铁片眼儿,绑鸡毛,缠塑料,点着塑料在砧板上搥平。不一会,美丽的毛毽就做成了。出去以后一个个吵吵巴火地比啊,玩啊,完全忘记了自己做过的“大事”。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作案的一干人被人家挨个找到家里,一般都挨了大人的笤帚疙瘩。怕我们再惹事,每年杀鸡的时候,家里大人都要把绑鸡毛掸子的漂亮公鸡毛给我们留点做毛毽。
想想被我们薅光了毛的公鸡的模样,在窃笑之余还是蛮同情的,我们这些毛孩子也真有点惨无人道了,大冬天的,让人家那只公鸡几乎在裸活。
现在每当看到孩子们玩毛毽的时候,那美丽的色彩常常让我想起童年里的一幕。幼稚的、可笑的童年像美丽的轻柔的羽毛渐飘渐远。也许我的童年故事在现在的孩子看来,就像我童年里薅过毛的那只公鸡一样可笑吧,一定的。
小链接时春华,今日朝阳网文化信使,现就职于辽宁省北票市教育局信息中心。1992年毕业于朝阳市第一师范学校,选修音乐,酷爱文学,文风朴实接地气。热爱生活,热衷传播社会正能量。系朝阳市作家协会、辽海散文学会、北票市作家协会会员;《好名声网》特约助理编辑,此网站有《时春华好名声展馆》;《北票市报》特聘记者,此报刊有专版《朝花夕拾》。在网络、刊物上发表作品600余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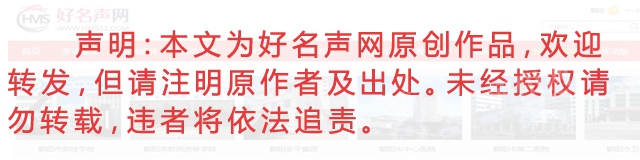
[编辑 安然]






 【好名声网】六一啊六一(时春华 杨晓芳)
【好名声网】六一啊六一(时春华 杨晓芳) 【好名声网】桃三杏四梨五年(时春华)
【好名声网】桃三杏四梨五年(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心中的尺子(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心中的尺子(时春华)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春灌(时春华)
【好名声网】记忆中的春灌(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的肩膀(时春华)
【好名声网】父亲的肩膀(时春华)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温馨家园开展“迎立春,闹元宵”文化体验活动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温馨家园开展“迎立春,闹元宵”文化体验活动 【好名声网】博览群书 一生充实(王铁兰)
【好名声网】博览群书 一生充实(王铁兰) 【好名声网】挂钱儿是大年的彩旗(时春华)
【好名声网】挂钱儿是大年的彩旗(时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