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敞开胸怀蕴梦想 向阳奔跑筑梦天地间
文图/石玉梅(辽宁朝阳)

我家的老宅如同一部血泪相容的史书,密密麻麻的窗格子上记载了祖孙三代人的艰辛历程。位于小村中央的老宅是祖爷爷留下的,共四间房,东屋一间为大,由爷爷、奶奶、小姑居住。西屋两大间是父母和我分别居住,中间一间是厨房。
老宅是完完全全旧式的土木格局,笔直的松木过梁承载着老宅的威严,排列有序的檩子和椽子默默地守护着老宅的温情。门前和房后那几棵高大的白杨树,挺直腰板像是卫兵站在那把守着。老宅院子狭长,院墙全部是从小村东部的山上捡回来的石块,用混合黏土一层一层堆积而成,像是用一种庄严和质朴激励石家后人不断进取。老宅的大门是两扇儿手拉的木质门,既古朴又庄重。大门上面的水泥锤顶门檐,构成了独特的门洞子,是炎炎夏日说话乘凉遮风挡雨的好地方。
老宅祖传一只黄褐色的手拉风匣,最少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还是奶奶当年使用过的。不知它拉进拉出了多少昔日的喜怒哀乐,现在已成为稀罕物,静静地躺在东屋回忆着逝去的日月。老宅房后和前院各是一块儿整齐的菜园子,有规化地种着几池子小葱、黄瓜、豆角、萝卜、大白菜等,用勃勃生机点缀和警醒着宅院的春夏秋冬。
爷爷说他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姐弟六人全靠给邻村地主刘文彩家种地交租维持生计。太爷爷生性耿直,又大字不识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刘文彩,阴险的刘文彩在租地文书上做了手脚,欺负他们目不识丁。太爷爷还像往年一样把租地文书拿回家放在了柜子里。碰巧那年秋收时下了滥场子雨,秋收延迟,交租子时晚了一月有余。当太爷爷准备好租子带着两个儿子去交时,刘文彩拿着文书说差了两石租。太爷爷一下子懵了,忙找来村里教书的先生念给他听,才明白刘文彩在文书上附加了两条:延期十天多交租一石,延期一月多交租两石。白纸黑字,太爷爷吃了哑巴亏,气得病倒在床。二爷爷、老爷爷听说气不过,去找刘文彩理论。刘文彩扬言要把两位爷爷告到官府吃官司。太爷爷被逼无奈,连夜让两个儿子逃走避难。谁知一去便是永别。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别数月,杳无消息。太爷爷思儿心切,一病不起,临终前拉着大爷爷和爷爷的手说:“一定要记住,以后家里面一定要出个读书识字的……”话没说完,含恨离世。
父亲的到来,点燃了爷爷儿时的理想,给爷爷奶奶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他们平时口积肚攒地把家里的干粮都留给了父亲,而两位老人靠吃荆条籽、树皮和糠菜充饥。1961年,年仅17岁的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年朝阳县东南部唯一的一所学校——松树咀速师班,这在全县是很有名气的学校。二年后,父亲毕业了,光荣地成为小村的一名教师。看着自己的孩子成了老师,爷爷说那时的心情睡觉都能笑醒,甭提有多甜了!

1970年,我的一声啼哭给老宅又带来了一丝欢笑,也加重了父母的负担。当时我已有两位姐姐,接着四妹,弟弟、五妹也相继来到世间。老宅一下子拥挤了好多。那时候教师的工资很少,虽然生产队额外给了公分儿,小队也按人口分了口粮,但日子还是捉襟见肘。子承父志,我的父亲在对待求学的事上一点不含糊。他利用业余时间与母亲辛勤劳作,用大高粱秆破成细篾,编炕席、编酱棚、编大锅盖、编水缸盖等,拿到集市上变卖贴补家用。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半夜一觉醒来,模糊的双眼看见父母西墙上煤油灯下晃动的身影,稀疏的听见他们编炕席沙沙的声响……
我的家乡地处朝阳市东南部,隔河与葫芦岛市相望。当年乡中所在地——根德乡中学,距离我们家十八里山路,那时没有大客车、电动车等可用的交通工具,全靠步行,跑不起还得住宿,又增加了开销。因为这些原因,全村的孩子十有八九辍学了。父亲却鼓励我们姐弟一定不怕吃苦,坚持完成学业。“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父亲坚信这一点。当年我们姐弟四个人同时上学。高中、初中、小学都有,原本不富裕的日子更加拮据起来。父亲鼓励我们不要有思想负担,不要有顾虑,把心思全部放在学习上。1986年清明节,爸爸在门洞左边栽上一棵槐树,在右边栽上三棵白杨树。当年,我曾好奇地问过爸爸,为何要栽这几棵树?爸爸说:“槐树的‘槐’与‘怀’同音,原因有三:其一,纪念先祖;其二,要石家子女不要忘记祖训;其三,要你们感恩新社会,有书念,有书读。白杨树中的‘杨’与‘阳’同音,有‘面向太阳’和‘茁壮成长’之意,希望你们承继书香世家,扬眉吐气,勇往直前……”
有付出就有回报。终于,我的大姐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从事教育工作;我临床医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乡级医院的大夫;我弟弟参了军,并且在部队入了党;我的小妹学习成绩一直优秀,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大连外国语学院,并且毕业后同年考入大连理工学院硕士班学习,成为小村以至于根德乡第一位研究生。
如今,我们姐弟六人均在老家的周边城市朝阳市、葫芦岛市、锦州市里工作并安了家。只有老爸老妈还在老宅子居住。每当我们姐弟回家,看到邻里乡亲羡慕的眼神,发出啧啧的赞叹声,老父亲的嘴角挂满了甜甜的微笑,眼眸中发出自豪的光,我深知那也是他的一个个梦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爷爷早已过世,父亲也迈进了古稀之年。但他看上去仍然精神矍铄,还念念不忘读书、写字,父亲的一手好字是小村出了名的。早些年,每逢春节,邻里乡亲排着队来找他写对联。父亲一边研墨,一边大笔一挥,尽展豪情,这一天也是他最为得意和自豪的日子。平日里一有空闲下来,便保持读书的好习惯。家里面的《毛泽东选集》不知被他翻看了多少遍。我们姐弟上学时的书他还部分地保留着,一得空便翻看着,每每读到兴奋处,情不自禁地朗诵着,情不自禁地仰着头说:“无事此静坐,有福方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老宅,经历了几世风雨,依然挺拔矗立在小村的中央。它用一种执着的信念和一双智慧的眼睛,鼓舞和教育它的后人们: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去追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原载于《营口日报》。

[助编 明月 责编 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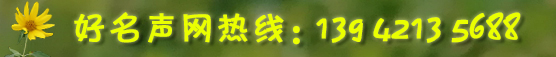


 【好名声网】母亲的“谎言”(包明丽)
【好名声网】母亲的“谎言”(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间烟火年味浓(杨广大)
【好名声网】人间烟火年味浓(杨广大) 【好名声网】我的菜 我的爱(包明丽)
【好名声网】我的菜 我的爱(包明丽) 【好名声网】鸡蛋,鸡蛋(李娜)
【好名声网】鸡蛋,鸡蛋(李娜) 【好名声网】展开梦想的翅膀(杨广大)
【好名声网】展开梦想的翅膀(杨广大) 【好名声网】火锅飘香(王铁兰)
【好名声网】火锅飘香(王铁兰) 【好名声网】流逝的缝补(管丽香)
【好名声网】流逝的缝补(管丽香) 【好名声网】场院(李兴坤)
【好名声网】场院(李兴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