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民探古寻踪
寻访古城遗踪——感受辽代石刻文化
文/陈玉民 编辑/安然

朝阳作为辽代的大定、兴中两府辖地,二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在这里留下大量的辽文化遗存。让我们看到最多的是辽塔,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砖刻,华丽的浮雕,无不彰显出辽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广博。每一座塔,都堪称是辽文化的一个坐标。每次临近辽塔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品悟一番辽塔所透露出的浓郁文化气息。从一块砖雕上,我试图读出辽代文化的厚重。从一种造像上,我试图品出辽代文化的深邃。欣赏辽塔,如同在眼前打开一扇观览辽代文化的窗户,令我对辽代文化充满渴望和向往。
正当我对辽代文化痴迷眷恋之时,另一种蕴含辽代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走入我的视野。宋晓珂先生的《朝阳辽代画像石刻》送至我的案头,我急不可耐地拿到手中进行浏览。这是一本专门反映辽代画像石刻的拓片图集,将在朝阳境内发现的比较典型的辽代画像石刻,都拓下来荟萃于一册,并配有实物照片。非常清晰地将留存于朝阳大地上的辽代画像石刻艺术,比较完整地展现出来。这是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反映辽代画像石刻艺术的一本图集。它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辽代画像石刻艺术,感受辽代石刻文化特色,设置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辽代文化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具有很强的民族宗教色彩。既能看到汉唐、北宋文化的多姿风韵,又能看到契丹王朝的文脉基因。辽代人极具文化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凭着对自然的热爱,对天地的敬畏,对神灵的崇拜,对生活的向往,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内心的追求,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辽代画像石刻艺术是辽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是辽代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所发现的辽文化遗存上看,辽代画像石刻遍布许多领域,与当时的社会审美、宗教崇拜、风俗时尚、价值追求息息相关。表现最突出的是在宗教领域,凡是辽代留下的宗教建筑、装饰、器物,都可看到其画像石刻的踪影。有东北第一塔之称的朝阳北塔,是辽代画像石刻艺术的集大成之处。天宫供奉佛祖舍利的石匣,内壁东面石板刻有法、报、化三身佛,北壁石板刻的是佛、菩萨像,石门刻的是是门神、飞天。这三块石板上的画像石刻,堪称是辽代画像石刻的代表作,构图精美,线条十分流畅。地宫的舍利石函,石盖及函身四侧,都有精美的画像石刻。石函盖上中间刻的是《心经》,四周刻的是飞天。石函外壁上环刻的是“大圣哪吒太子追杀和修吉龙王”的佛传故事。哪吒头戴火焰冠,身穿甲胄,脚踏祥云,左手托塔,右手向前作指挥状。哪吒前面为五夜叉,或摇旗呐喊,或擂鼓助威,或举剑劈杀,或张弓射箭。龙王纵身疾驰,前后受箭,一箭射中后腿,一箭射中腹部。八个有首无身的小龙紧随其后。十分生动,惟妙惟肖。由于地宫早年被盗,石函盖遭到破坏,使得这个精美的石刻艺术品留给我们的是一幅残缺的美。地宫石经幢,是北塔留下的又一辽代石刻精品。其经幢座、经幢盖、经幢身,随处可见有精美的石刻画像。幢座第一节第一层侧面雕刻的飞天、盆花,上面雕刻的是伎乐童子及缠枝花纹。第二层雕刻的是八大菩萨。第二节幢座雕刻的是过去七佛、执金刚神众。第三节幢座雕刻的是八大灵塔及七佛名。第四节幢座雕刻的是八王分舍利。经幢盖顶雕刻的是飞天、单层方塔、衔枝鸟、迦陵频伽。刻划方法为剔地浅浮雕,刀法圆润、线条优美,图像逼真,意境深远。幢身用汉文及梵文刻写佛经咒语,采用的是阴刻楷书。雕刻如此精美的天宫、石函、石经幢,见证的不仅是辽代石刻画像艺术的繁荣,而且也反映出朝阳辽代时期佛教的兴盛。在一座塔里,竟然用如此精美的石刻画像,来衬托佛祖舍利供奉的场所的豪华、奢侈,来表达供奉者对佛祖的慷慨、虔诚。
槐树洞石塔,是辽代石刻画像用于礼佛供佛的又一典型力作。此塔虽已不完整,但从残存的三级塔身上,我们依然能读到这座石塔雕刻的精美。第一级塔身是用八块刻有壸门及兽面、瓶花图案的石板围栏的。第二级塔身是用八块刻有呼之欲出的伏狮头像的石板垒砌的。第三级塔身是用八块刻有脚踩莲花的乐舞伎人物的石板构建的。这种八角形空心石塔,或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当在塔身上雕刻出精美的石刻画像后,就显得石塔的不同寻常了。它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古塔的建造形态,而且还让我们感受到了辽代石刻画像艺术给佛教建筑带来的精彩。
除了在佛教场所的塔、碑、幢、函上能见到精美的辽代石刻画像外,在辽代墓地也发现许多石刻画像。最典型的是石棺,朝阳境内的每个县几乎都发现有辽代石刻画像的石棺。这些石棺,在石料的选用、画像的雕刻技法、表意构图上,都十分讲究。凌源市八里堡村上喇嘛沟村出土的石棺侧档板为三块雕刻石板,第一块雕刻的是散乐图、牵马图、仪卫图。第二块雕刻的是围猎图、射猎图、停歇图。第三块雕刻的是牵畜图、牛车图、仕女图。这九组浮雕图,是对墓主人生前娱乐、出行、狩猎等日常生活的描绘写照,也是对墓主人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一种寄托,希望能延续在世时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喀左县于杖子村发现的石棺,上面的石刻画像表达的是孝悌内容。十二块石板上可辨认的故事有:王祥“卧冰求鲤”、郭巨“为母埋儿”、董永“卖身葬父”、杨香“救父打虎”、黄家瑞“割股医母”、姜诗“涌泉跃鲤”等,这些都是《孝子传》和《二十四孝》里节选下来的经典故事。虽然人物穿着改成了契丹服饰,但故事内容没有改变。汉族所推崇的孝悌故事,得到契丹族的追捧,这可看作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个例证。喀左县老爷庙乡杨树底下村出土的画像石棺别具特色,棺体呈长方形,前高后低,前宽后窄,置于围栏式基座之上,仿硬山式建筑风格。盖石为两面起坡起脊,坡面各刻莲花四朵。石棺左右后壁分别雕刻青龙、白虎、玄武。前壁上部刻朱雀,两侧为正式莲花,下部中间刻一门,两侧分别为二人奏乐,四人装束相同,头戴毡帽,身着长袍,腰系布带,脚穿高靴,手持乐器。这是一个比较豪华的石棺,普通的百姓逝去恐怕难以享用。
辽代的石刻墓志也比较考究。朝阳县黄道营子的墓志除了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平外,盖顶上下及四周还刻有牡丹、十二生肖像、云纹、日、月、星、八卦等精美的图案,这当是辽代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墓志。
辽代的石刻画像艺术的运用,绝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这或许只是其中最常见的几种形式。由此我们不难想象,辽代是石刻画像一定是浸润到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人们表达情感,寄托思念、抒发情怀,铭表心灵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方式。一个场景,有了石刻画像,就会多一种浪漫;一种建筑,有了石刻画像,就会多一种情调;一件物品,有了石刻画像,就会多一种精彩。可以想象,由于辽代重视石刻画像艺术的运用,辽代人的生活情调一定是丰富多彩的,辽代人的生活场景一定是高雅绚丽的,辽代人的生活追求一定是完美时尚的。
小链接



 【好名声网】密州的诗酒年华(李亚男)
【好名声网】密州的诗酒年华(李亚男) 【好名声网】春风十里 温情几许(李亚男)
【好名声网】春风十里 温情几许(李亚男) 【好名声网】雨落成诗(李亚男)
【好名声网】雨落成诗(李亚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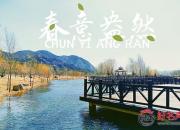 【好名声网】立春感怀(李亚男)
【好名声网】立春感怀(李亚男) 【好名声网】书香盈心(李亚男)
【好名声网】书香盈心(李亚男) 【好名声网】写给可爱的小天使(三)(李亚男)
【好名声网】写给可爱的小天使(三)(李亚男) 【好名声网】喜迎二十大 同心向未来(李亚男)
【好名声网】喜迎二十大 同心向未来(李亚男) 【好名声网】花开云舒(周显梅)
【好名声网】花开云舒(周显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