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东北话系列
“炕”从“外头”来(十)
文/吴歌 编辑/寻冬

无处不在的“炕”,堪称“外头”(关外)的物质和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化身”。
然而,无论坊间还是学界,对《红楼梦》中的“炕”都存在诸多的不解、误解和曲解。
品读“炕”之怪论,着实令人感到怪之又怪。因乎未见“灶”和“烟囱”的描写,便断定“炕”不能烧火;因乎有“火盆”和“熏笼”等的存在,便断定“炕”不能取暖;因乎不了解“炕”上生活,便断定铺有毡子的必是“凉炕”……
不能烧火,李纨的“地炕”莫非要抬到屋外去“爖”?若非凉“炕”,便不需要“火盆”或“熏笼”等?东北翁媪围着“火盆”所坐,莫非都是凉炕?“炕席”(芦席)上铺毡子,在黎民百姓家也不足为奇。贾府“炕”上铺着洋罽和兽皮褥子,不过是有钱人家小小任性之举罢了。
愚以为,刻舟求剑式地解读任何文学作品,都会令文学失去立足之地。
没写“爖火”和“日出”,便不能写“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
仅仅登上鹳雀楼,焉能同时见到“白日依山尽”和“黄河入海流”?“白日依山尽”所依之山,应为西山;“黄河入海流”之海,应属东海。如果没有进入太空,谁能看见西山与东海“同框”?
聂桥《<红楼梦>中炕的怪现象》(人文化 百家号 2017年7月15)谈到“炕”之“怪”,主要怪在北方之“炕”与南方之“竹”能够“同框”。“若说大观园在北方罢,何以有‘竹’?若说贾家在南京罢,何以有‘炕’?”是聂桥先生文中所言“老一辈的红学研究者”顾颉刚和俞平伯在通信中讨论过的问题。
至此,不才我想到了即将发行的高铁币。据悉,央行将于2018年9月3日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一枚。背面图案包括复兴号动车组、大胜关长江大桥、北京南站、高山、梯田、沙漠等。用“老一辈的红学研究者”的眼光看,会否也是“怪现象”?若说复兴号动车组在北京罢,何以有南京的“大胜关长江大桥”?若说复兴号动车组在南京罢,何以有北京的“北京南站”?
“艺术家为了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美感效果,在一定的空间,安排和处理人、物的关系和位置,把个别或局部的形象组成艺术的整体。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称为‘章法’或‘布局’。”——《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年)中“构图”之释文,也应该适用于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岂能没有“章法”和“布局”?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的艺术个性》(个图书馆 2015年11月16日)中,谈到过整个《红楼梦》的“大布局,大章法”。
江南的“竹”,“外头”的“炕”,共同“植入”都中的“园”,因何不是“大布局”和“大章法”?
否则,《红楼梦》在地理背景上的“布局”和“章法”之“大”,是否连小小的高铁币都赶不上?
小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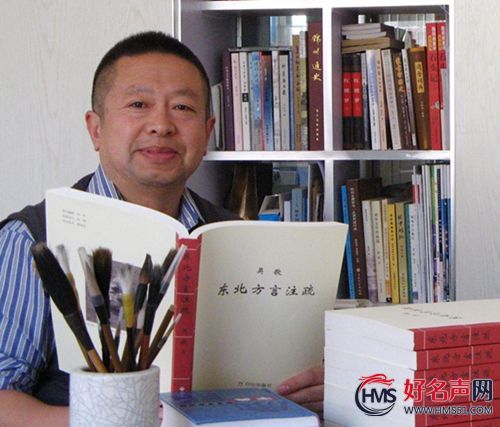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