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东北话系列
“炕”从“外头”来(七)
文/吴歌 编辑/寻冬

无处不在的“炕”,堪称“外头”(关外)的物质和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化身”。
“搭好烟道后,上面再用一层单土坯盖上,土坯上面再抹上黄泥,然后从大炕的灶坑里填柴火烧炕,一会儿你就会看到整个炕面烟雾缭绕,不过炕面有些缝隙还会往外冒烟,这时还得用黄泥勾缝填泥。待火炕的炕面烧干了以后,铺上用高粱秆编的炕席,在炕的最外边缘处钉上一整根木头,为炕沿,就可以睡人了。”——黑龙江日报(2016年11月26日)《北方的火炕》。顺便说下。“高粱秆”,应指“高粱篾”;“柴火”,应指“柴穫”。柴与穫,近义并列。
如今,“土坯”,可用砖或水泥板代替;“黄泥”,勉强也可用水泥代替。之所以说“勉强”,是因为“黄泥”弄不到。试想,如果有紫砂茶具,谁会接受水泥的?
“炕面子”抹“黄泥”,还能令“扒炕”时不似水泥那么费劲。“炕洞”里累积的焦油和烟灰,会降低排烟和取暖效果,需要定期清理。“扒炕”,实指将“炕面子”扒开以清理“炕洞”。如:
“除了种地外,家中的扒炕、抹墙、推碾子拉磨等重活都是他的事。”——凤凰网(2016年3月20日)《父亲、母亲和哥哥,我对你们都有愧疚》
没铺“炕席”之“炕”,都叫“土炕”,相当于“裸炕”。编芦席的睡土炕,卖咸盐的喝淡汤。俗语之义,在乎揶揄无暇自顾者。所以,“土炕”,不是贫苦的代名词。
“……晴雯睡在芦席土炕上,幸而衾褥还是旧日铺的。”——《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第七十七回。既有“芦席”,又有“衾褥”,并非“裸炕”。为强调宝玉的怜惜,说晴雯睡在“土炕”上,反而导致细节失真。
“炕面上要先铺一领大炕席,再铺一床厚厚的棉炕垫子,然后铺上羊毛炕毡,最后罩上线织的大炕单,它的四周有穗儿,其底色和大团花图案,多为墨绿、紫红和熟赭色,耐脏、美观又结实。”——北京晚报(2018年1月27日)《冬天睡热炕那叫一个棒》
“晚上睡觉时另铺褥子、褥单,冬天盖棉被、毛毯等。白天把被褥叠成‘豆腐块儿’,摞在炕脚靠窗处,外边盖个布单儿,外观像个‘箱子’,叫被活垛。”——同上。顺便说下。“被活”,应为“被幄(wo)”之变读。
有些方家,或许很懂《红楼梦》,却不很懂“炕”或曰“火炕”。
土默热红学《<红楼梦>中的炕不是火炕是炕榻》(新浪博客 2015年4月19日)认为,“火炕需要散热暖屋,平时炕上只有芦席(俗称炕席),白天不能用炕褥遮盖,晚上睡觉时才能铺褥子。”断定“炕褥”以及“洋罽”(jì。义犹毡)和“条毡”等,在“北方火炕上是没有的”,概因土先生没有见过真正的“北方火炕”。
其实,“炕”上所铺之物越多,越能延缓热量的释放,越能彰显主人的家境。
小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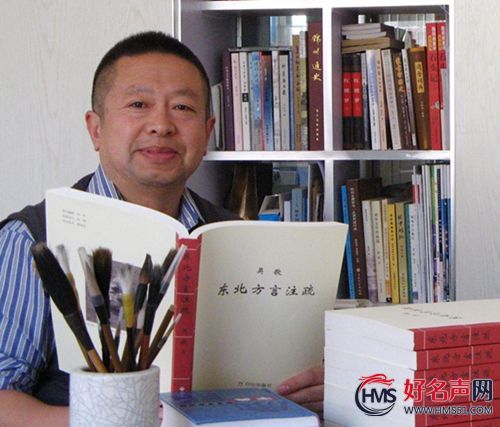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