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东北话系列
方言不等于“土话”
文/吴歌 编辑/寻冬

孙良 摄
鲁迅先生说过,读《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因乎(yōng hu/wu)啥“家”也不是,不才我读《红楼梦》,只能看见方言——东北这“圪塔(gā da)”的方言。“圪塔”,音同“疙瘩(gā da)”。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古诗文网)。身为“南人”的颜之推,如此抑南扬北,应该不是出于地域偏见吧?
东北话中为数不少的“古语”,或因被当成“土话”或“土语”,而疏于考证。
“被幄(bèi wo)”,在《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中被讹作“被窝”,在尹世超主编《东北方言概念词典》(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0年)中被讹作“被卧”。
“被窝(bè wo)”,被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留作“飞白”。是有意回避?还是无意疏失?
幄,“帐也。帱也。大帷。覆帐谓之幄。”——《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引证《小尔雅》之“覆帐谓之幄”,已经“点”倒“覆盖”之义。且不说,帱,亦“覆也”;覆,亦“盖也”。而“被”,亦即“被也,被覆人也。”——同样出自《康熙字典》
东北人都(dóu)知道,“被窝(bèi wō)”,是可以钻的;“被幄(bèi wo)”,是用来盖的。
南方看官“若(yào)”想整明白啥叫“老太太钻被窝”,来东北的冰上“走两步儿”,“摭(zhǐ)不定”就能获得切身的体验。
当然,错过冰天雪地,还有东北之“春”。
春,蕴含无限的美,也蕴含无限的色(shǎi)。春宫,因其傍着“宫廷”而得“春”之名;春话,因其出自“草野”而染“村”之声。
“撒春(sǎ chūn)”,属于东北话中“较(jiǎo)比”温和的说法。较比火爆的,是“攋(lǎi)春”甚至“攋大春”;更加火爆的,是“攋膘”甚至“攋大膘”。“膘”,义即关乎“皮肉”之事。尹世超主编《东北方言概念词典》作“彪”,或需推敲。
《红楼梦》中的“撒村”和“撒村捣怪”之“村”,原义应属“春话”之“春”,并非“假语村言”之“村”。
东北“辞多古语”,比(pǐ)颜之推所云“山川深厚”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文化积淀的“深厚”。
东北,古称幽州。当代的东北话,应该是先秦幽州话的延续。
辽宁西部(非辽河以西)的大小凌河流域和医巫闾山麓,是先秦幽州文明的核心区。八千多年前,渔猎农牧各类文化开始在这里碰撞融合,使这里成为“中国各主要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中,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据2012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辽西或是我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区域》)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唐]金昌绪之《春怨》,同时又叫《伊州歌》。无论是作为副标题还是作为“乐府曲调名”,“伊州歌”之“伊”,因何不是“医巫闾”或曰“医无闾”之“医”呢?
“医巫闾”或曰“医无闾”,几千年前就拥有“幽州镇山”的称号。她,不仅是幽州文明的见证,也应该是幽州文化的基因。
注释:方言相关内容,依据拙作《东北方言注疏》(白山出版社 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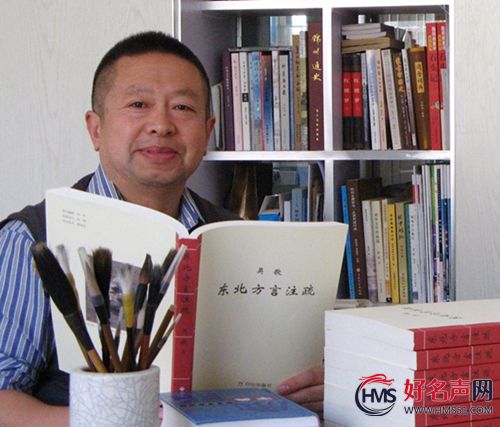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