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五台山”去干何(há)
文/吴歌 编辑/寻冬

孙良 摄
《红楼梦》第二十二回,贾母斥银二十两令凤姐为宝钗过生日,惹来凤姐一顿调侃:“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说得满屋里的人“都笑起来”。顺便说下,“梯己”,应作“体己”——体恤自己。
“上五台山”,去干何(há)嗫?
依周汝昌先生《红楼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的解释,是“登仙成佛”。既“上五台山”,就能“登仙成佛”,是否想当然?
这回书的题目,就叫《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上五台山”说法本身,应该蕴含禅机。结合贾宝玉的命运来考量,应该属于禅机。
从东北话的层面解读,“上五台山”或“顶上五台山”,含有报恩的口惠而实不至之义。如:
“指望他报答你,你就等着上五台山吃猴儿屪子吧。”——拙作《东北方言注疏》
“顶五台山吃猴儿辽(屪)子这说法,小时候常听到”。——赵鑫先生(辽西方言帮 微信群友)所言“顶(上)五台山”,与“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如出一辙,更能证明“登仙成佛”的莫须有。
既是东北话,为啥不说上兴安岭,却说上五台山呢?
因乎(yōng hu)五台山在山西。而山西,在东北方言体系中,属于世界上最远的地方。
《去老远山西,看大同小意——十一假期山西文化自由之旅》(蚂蜂窝 2016年12月13日),来自铁岭的日月先生的文章的标题,带有搞笑意味。因为老远山西,通常是作为形容词使用的。如:
老远山西的南极,去一趟着实不易。
老远山西,究竟有多远?恐怕比爪哇国还要远。爪哇国,远;山西,“老”远。
之所以远,概因为文化差异。
虽然“同居”北方,山西话于东北人来说,与外语无异。据康熙年间的《山西通志》记载,外来官吏“每见听讼者,官诘于上,民不解;民诉于下,官不解。不得不藉传于胥役之口,胥役传官之话于民,官仍不解,传民之话于官,民仍不解。”
于长城,东北的“关”,山西说“口”;东北地被“闯关东”,山西人去“走西口”。闯,豪迈;走,悲凉。在球场,东北人喊“捎他”(捎,方音为xiāo。非削),山西人吼“闹他”。捎,芟也;击也。闹,不静也;猥也,扰也。捎,闹,音义均据《康熙字典》。
文化的差异,宛若无形的鸿沟。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山西人侃侃而谈,东北人却不知何意!(套用泰戈尔诗)
回头再说《红楼梦》。谭汝为《<红楼梦>方言研究浅议》(今晚报 2016年1月7日)认为,《红楼梦》全书所涉及的方言非常复杂,但主要使用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官话京腔”。可是,所谓的“官话京腔”,从何而来呢?
中国日报(2016年7月29日)《北京话并非来自满语 南京官话、盛京官话是其源头》和凤凰网(2011年07月18日)《北京话历史:清代中叶形成 许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等,阐明了北京方言的源流。两篇文章的出处,都是北京晨报;两篇文章的依据,都是北京史志。
注释:方言相关内容,依据拙作《东北方言注疏》(白山出版社 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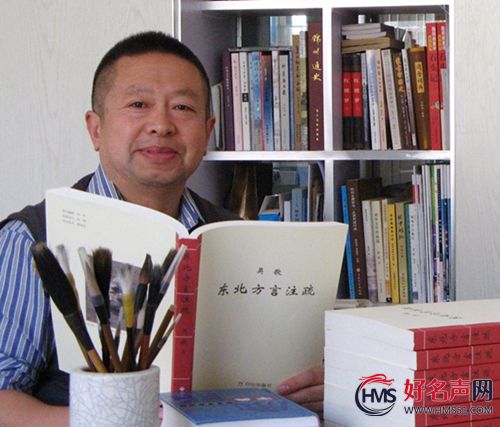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