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东北话系列
“戚(qiě)”自逻辑来
文/吴歌 编辑/安然

名副其实属血亲,
当仁不让是姻亲。
血亲姻亲都不是,
水亲土亲谓乡亲。
熟人社会里,沾边儿即可称“亲”。乡亲的“班底”,当属“屯亲”。东北话里,屯,义犹村(庄)。“屯亲”,即“屯论儿(lìr/lìnr)”之“伪”亲属——拐弯磨角“盘”上的亲属。磨,磨车之磨,磨身之磨,非抹。
“盘”辈儿过程中避低趋高,叫作“攀大辈儿”。“攀大辈儿”,往往令对方心生不悦。因而有“攀大辈儿没好事儿”之说。“盘辈儿”,延伸至江湖,谓之“盘道”。
所谓“屯论儿”,就是将本屯乡亲的关系“论”到血亲或姻亲关系上,彼此再以“论”出之亲缘相称相谓。
不亲假亲,也叫“攀亲”。称顾客为衣食父母,是否也属“攀亲”呢?
“攀亲”,于淘宝店家,称客为“亲”;于东北店家,称客为“戚(qiě)”。
拙作上篇《“戚(qiě)” 从入声来》,对“戚(qiě)”之得音理据做过交逮(逮,非代或待)。其中,地处环渤海“方言圈”上的济南,读“戚”如“qie”,读“客”若“kei”。
东北话中,“戚”或“客”之争的实质,表面在语音,实质在逻辑。如:
“‘大哥大姐请慢走!’送客送到门口,让你不得不记住‘翠花’,记住下次再来。”——新浪(2011年11月14日)《坐炕头见老妹 吃的是咱妈做的饭》。文章所言“大哥大姐”对应的“老妹”甚至“咱妈”,皆出自“主戚”关系,而非“主客”关系。作为元素的“大哥大姐”乃至大叔大姨甚至大姨父等,应该属于“戚”之集合,而非“客”之集合。或者说,“大哥大姐”乃至大叔大姨甚至大姨父等的统称,应该是“戚”,不应该是“客”。“客”,没有任何亲缘,连“套”出的亲缘都没有,其统称也应该是“客”。
“……从词意分析,这个‘客’字没有体现出东北人对客人的那种如亲人、亲戚般热情、火辣、豁达的情感,而‘戚’(读qiě)字却十分准确地表达了东北人对客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情感。因此,在词典中‘来戚’一词,用‘戚’而非‘客’来表述是符合其意境的,应该是准确的。”——人民网(2014年3月3日)《<东北话词典>:十载记录原汁原味的东北话》。该文作者高永龙先生,没有提及逻辑关系,却在“词义”和“意境”上为逻辑关系提供了佐证。
“戚”,本义应为到访之“戚友”,或曰前来“串门”之“戚友”。“俗谓戚友往还曰串门”。——金毓黻《奉天通志·方言》(辽海出版社 2003年)如是说。“戚友”,当今东北话谓之“亲友”,晋源方言谓之“戚人”。“戚人”,音犹“ciē/qiē rēng”。“ciē/qiē”,读音短促。
“戚”或“客”,在语用上并非没有差异。“老戚儿”,用以揶揄套路生变之亲朋;“老客儿”,用以称谓外来行商(非坐贾)之主顾。“客爷”之称,有;“戚爷”之谓,无。等等。
注释:方言相关内容,依据拙作《东北方言注疏》(白山出版社 20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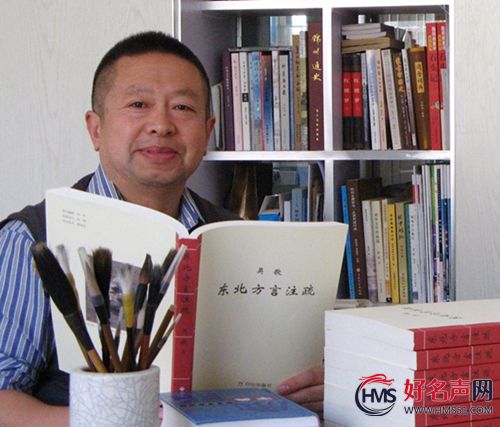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忘了真好(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名字趣谈(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人海拾贝(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婚姻碎语(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幸福的回忆(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春暖花开见“彩虹”(包明丽)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最美四月天(刘莉)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
【好名声网】爆竹虽无声,春风仍送暖(包明丽)